 杨冰
杨冰 2025年,国内医师执业制度迎来重大变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多部门发布《关于深化医师多点执业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具有副高级以上医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在该技术职务上连续执业满2年的医师,可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不超过3个医疗机构开展多点执业”。这一政策突破地域限制,标志着我国医师多点执业进入“全国流动”新阶段,为医疗资源均衡分配、分级诊疗体系完善注入新动能。
一、政策破冰:从“试点探索”到“全国铺开”的十年演进

医师多点执业并非新事物。早在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便提出“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2011年,原卫生部启动试点,允许中级职称以上医师在省内多点执业;2014年,国家卫计委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取消执业地点数量限制,探索区域注册;2021年《医师法》实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医师经注册后可在两个以上医疗机构执业”;2025年新政则进一步打破省际壁垒,实现“全国一张网”。
政策突破的核心逻辑:
技术支撑:电子病历共享、远程诊疗系统、医保跨省结算等信息化手段的普及,为医师跨区域执业提供技术保障。
需求驱动:基层医疗机构人才短缺问题突出。据统计,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仅为3.04人,且70%集中在城市三级医院,而县域患者外转率超30%。
国际经验:美国、英国等国家允许医师在多个医疗机构执业,通过市场化机制调节医疗资源分布,为政策设计提供参考。
典型案例:
深圳先行:2015年,深圳率先取消医师多点执业需优先执业地点审核的环节,改为备案制。截至2025年,深圳注册医师中超40%开展多点执业,基层医疗机构门诊量年均增长15%。
北京模式:北京协和医院与河北多家县级医院建立“医联体”,通过多点执业输送专家,使河北患者县域就诊率从62%提升至78%。
二、新政核心:副高医师“全国执业”的资格与规范

(一)准入条件:严把质量关
新政对副高以上医师多点执业设定严格门槛:
职称与年限:需取得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且在该职称上连续执业满2年。
能力评估:需通过省级卫生健康部门组织的“多点执业能力考核”,包括临床技能、医患沟通、医疗安全等模块。
协议管理:优先执业地点医疗机构需与第二、第三执业地点签订《多点执业合作协议》,明确责任划分、利益分配、纠纷处理等条款。例如,广东规定协议需包含“医疗事故责任承担比例”“医师出诊时间保障”等内容。
(二)执业范围:全国“一盘棋”
地域限制解除:医师可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执业地点,但需在当地卫生健康部门备案。例如,上海瑞金医院的心外科专家可同时在四川华西医院、云南某县级医院执业。
执业类别与范围一致:多点执业的类别(如临床、口腔、中医)和范围(如内科、外科)需与优先执业地点注册信息一致。
基层倾斜:鼓励副高医师到县级以下医疗机构执业,对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多点执业的医师,给予职称评审加分、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三)监管机制:全链条闭环管理
注册信息联网:医师多点执业信息纳入“国家医师执业注册管理系统”,实现全国实时查询。
定期考核:医师需接受各执业地点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互通。若在任一执业地点考核不合格,所有执业资格将被暂停。
信用惩戒:建立医师执业信用档案,对违规转介患者、超范围执业等行为记入不良记录,影响职称晋升和多点执业资格。
三、政策影响:医疗资源“下沉”与行业生态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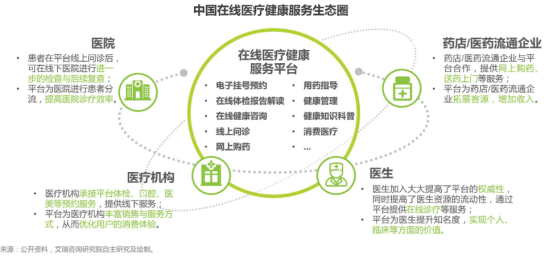
(一)患者获益:家门口看“大专家”
新政直接缓解基层患者“看病难”问题。以云南省为例,2025年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中,多名副高以上中医专家通过多点执业到县级中医院坐诊,使当地患者无需长途奔波即可接受传统中医治疗。据测算,政策实施后,县域患者外转率可下降10%-15%,年均节省医疗支出超百亿元。
(二)医师价值释放:从“单位人”到“社会人”
多点执业为医师提供“第二收入渠道”。以广东为例,副高医师在基层医疗机构多点执业的日均报酬可达2000-3000元,远高于公立医院平均水平。同时,医师可通过跨机构执业积累临床经验,提升学术影响力。例如,北京某三甲医院肿瘤科主任通过多点执业参与多家医院的MDT(多学科诊疗)团队,其研究成果被国际顶级期刊收录。
(三)医疗机构转型:从“竞争”到“协同”
大医院“松绑”:优先执业地点医疗机构需支持医师多点执业,不得设置不合理障碍。例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明确规定,副高医师每周可安排1天到基层执业,其绩效工资不受影响。
基层“强基”: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提升服务能力。云南某县级医院引进省级眼科专家后,年开展白内障手术量从200例增至800例,患者满意度达95%。
社会办医“激活”:民营医疗机构成为医师多点执业的重要目的地。2025年上半年,全国民营医院副高医师占比从12%提升至18%,专科优势逐步显现。
四、挑战与对策:平衡“流动”与“安全”

(一)医疗质量风险:如何避免“走穴”变“走样”?
问题:部分医师为追求经济利益,可能减少在基层的出诊时间,或让低年资医师代班,影响服务质量。
对策:
技术监管:通过人脸识别、诊疗记录溯源等手段,确保医师本人出诊。
患者评价:将患者满意度纳入多点执业考核指标,对评分低于80分的医师暂停资格。
保险兜底:推广“医师多点执业责任保险”,由医疗机构和医师共同投保,降低医疗纠纷风险。
(二)优先执业地点矛盾:如何平衡“放”与“管”?
问题:部分公立医院担心医师流失,通过设置考核指标、减少绩效分配等方式变相阻止多点执业。
对策:
政策引导:将支持医师多点执业纳入公立医院考核体系,与院长年薪挂钩。
利益共享:探索“技术输出分成”模式,允许优先执业地点从医师在基层的诊疗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管理费。
人才梯队建设:通过“导师制”“团队诊疗”等方式,减少对个别高层次医师的依赖。
(三)基层承接能力:如何避免“专家下乡,水土不服”?
问题:基层医疗机构设备落后、团队配合不足,可能限制高层次医师发挥作用。
对策:
资源下沉:中央财政设立专项基金,为基层配备CT、胃镜等基本设备。
团队建设:要求多点执业医师与基层医师组成“1+N”团队,通过带教、查房等方式提升基层能力。
远程支持:建立“省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远程诊疗平台,为多点执业医师提供实时技术支持。
五、未来展望:从“多点执业”到“自由执业”的渐进之路
新政的出台,是国内医师执业制度从“管制”向“治理”转型的重要标志。下一步,政策可能向以下方向深化:
职称评审改革:将多点执业经历纳入副高以上职称评审的加分项,鼓励医师到基层服务。
支付方式创新:探索“按病种付费+多点执业绩效”的复合支付模式,激励医师优化诊疗方案。
法律保障完善:修订《医师法》相关条款,明确医师在多点执业中的权利义务,减少法律纠纷。
结语
副高医师全国范围多点执业,是国内医疗体制改革“破壁垒、促流动”的关键一步。它既为医师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患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然而,政策落地需兼顾“效率”与“公平”,通过技术监管、利益协调、能力提升等手段,确保医疗质量不降、基层服务不弱、医师权益不受损。唯有如此,才能让“全国执业”真正成为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推动健康国内建设的“金钥匙”。





















